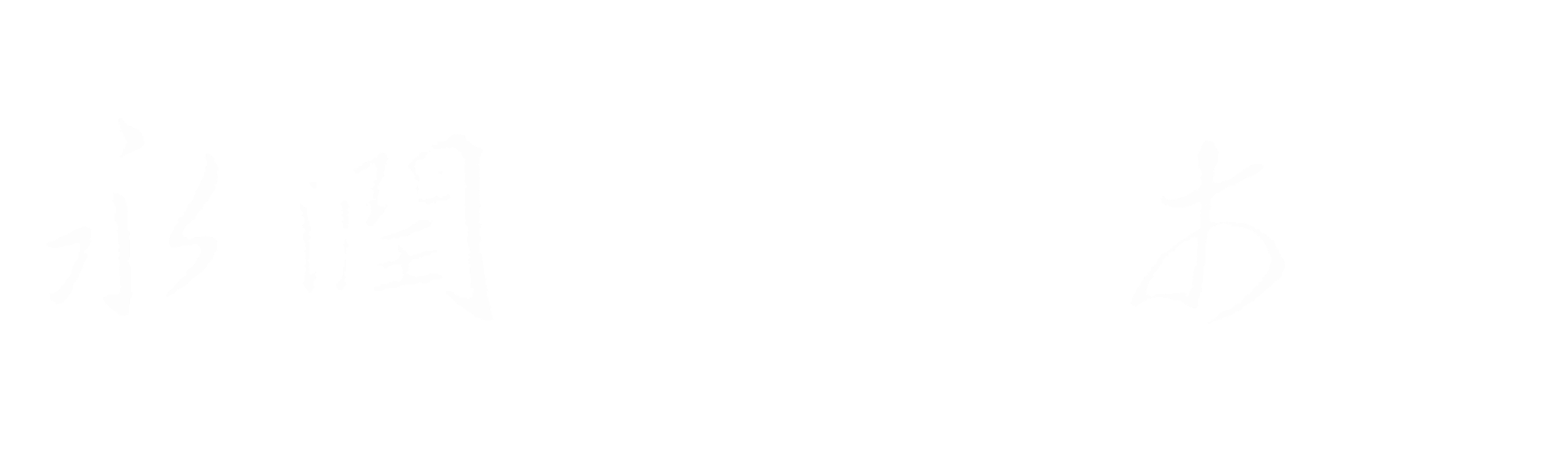此文为康大海别处投稿的再发。
“欣赏艺术作品时的某种愉悦感的体验似乎是从古至今没有变化的,这种愉悦感是一种广义上的愉悦感,比如看到一件作品而感到困惑并进行思考之后感到一种愉悦,又比如某个作品乍看上去会感到生理性不适,但之后想想又觉得挺有意思的”(摘自交流会微信公众号250325文章本文)
欣赏艺术作品时的愉悦感似乎可以解释为审美冲动,也可以和Eros放在一起考察。所谓Eros是一种本源性的冲动,是一种人的基本能力。例如一件艺术作品所触发的感性的审美冲动也许可以如此理解。“有趣”,“好玩”,“感动”,“愉悦”甚至“恐怖”等诸多冲动是否都能够被理解为同一种审美冲动所触发?
“成员接着愉悦感这一点来聊,他提出一个思想实验,假如人类没有任何感官感受,那么人类可以仅凭思维创作艺术、理解艺术吗?这恐怕是很难的。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,那么似乎感受性是进行艺术与欣赏艺术的基本条件之一。” (摘自交流会微信公众号250325文章本文)
假定人类没有感官感受的思想实验似乎有一些极端。他者无法在这个思想实验中进行有效的观测,来确定此人是否真的,仅凭思维进行了创作。这有一些像另外一个思想实验的例子,即,一个人能否在天生没有五感的情况下获得理性思考的能力。又进一步说,他的思考是否是基于语言的?也许这就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了。
“如果拿某个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放置在某处,这是否就是艺术品呢?如果使用科技手段投影出某个极其普通平常的物什(此物并非实存),这是否是艺术品呢?以及如何理解由技术手段制作的产品(如果这并非是审美作品,而是实用品)能否可以被归纳为艺术品呢(譬如提交建模后使用3D打印技术生产某个物品)?” (摘自交流会微信公众号250325文章云奕寄稿)
能够唤起审美冲动艺术作品,一般认为其具有一回性和崇高性。这两点本雅明的光晕论有阐释。所谓一回性,即时间和空间上的唯一性。没有复制技术的年代,这相对容易理解。所谓崇高性,假设我们简单地理解,可以唤之神性,也不用过多阐释。20世纪复制技术高度发展的年代,艺术作品逐渐丧失了这种光晕,成为一种可以被大量复制的商品。但是本雅明却并没有特别的悲观,认为这种光晕的丧失可以带来一定程度上的“世俗上的启示” (当然阿多诺却对此有不同看法)。摄影成像技术的黎明期,还不是一项可以大量复制的技术。长时间的曝光,将时间和空间都凝缩在一张底片上。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,这种带有光晕的早期写真逐渐地可以被大量复制。伴随大量复制,虽然艺术作品的光晕逐渐褪去。*关于这段有时间再详写。
如今是一个生成技术的年代。艺术作品不再是人造物,复制物,而发展成为一种物造物。物造物的机制,当然,还需要另加哲学上的考察。物造物是否具备一回性/崇高性的光晕特征呢?很难去说他们有。艺术家们对物造物“没有灵魂”的批判也许就是不需要佐证的佐证。然而本雅明乐观的“世俗启示”却依旧值得继续的观察。
“如果你对我上面的描述多少有一定的认同感,那么,屎,也的确是一种食物咯?你别说,还真有可能,在短视频刚开始发迹的时候,快手上有一位博主,名为岛市老八,他有三个爆火的短视频,就是旱厕吃此物,曾经获得过滔天的流量,随后被禁,但并不妨碍自身的热度,我也有理由相信他从中获得了不小的红利,而这份红利以及关注度肯定也给他带来了心里的愉悦,那我可以说,老八吃此物的行为,加上一个短视频传播的动作,就有可能会给他带来愉悦,那,此物,到底算不算一种食物呢?这里就可以链接到我的下一个主题了,也就是,我个人认为,屎,可以算作后现代的一种食物。” (摘自交流会250316Theo寄稿)
老八吃小汉堡,倒不一定是一种审美情趣,更可能像是一种“荒诞”。这自然是后现代的,一种非理性的复权。个人认为加谬和卡夫卡是此中高手(当然“魔幻”和“荒诞”的严格区分可以再议)。老八吃小汉堡,若是诉诸理性,可以归结于严密的功利计算,可以说是一种工具理性的使用。但是当仔细观摩多次之后,笔者始终挥之不去一种荒诞感。这和萨特的《恶心》描述的有些类似。老八有吃和不吃的自由,他在这种自由里泛着一阵又一阵的恶心。
康大海 于川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