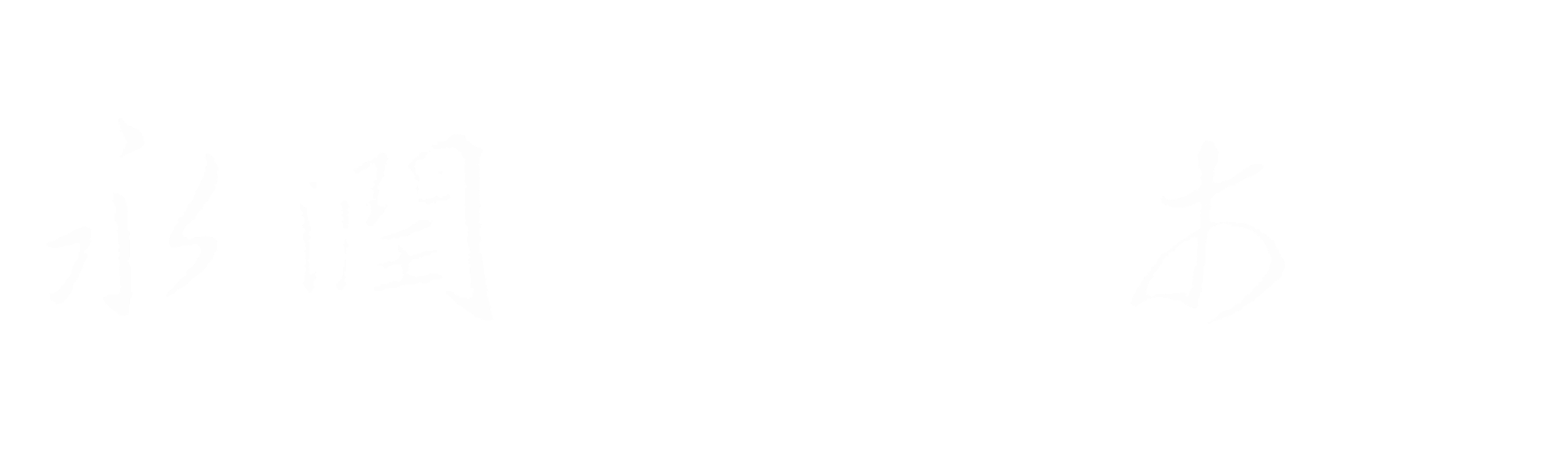陬访老人:
你犯了错,你想要逃跑。
你找到你最忠挚的朋友,和他说告别。
也是和自己说告别。
可,你就连告别也没法吐露无余。
但,你终归向你的朋友交出了你最后的诚实。
你无法说出的告别,
由朋友替你说。
特里,你坐在那儿。
一股香水味飘来,
你像一只幽灵,
迟迟不舍离去。
是的,我们也要告别了,伙计们。
越吵闹的时刻,
越舍不得说再见。
我注视着你离开,
直到你的身影消逝不见。
我依旧注视,
直到整个世界缩小成你。
陬访老人:
你犯了错,你想要逃跑。
你找到你最忠挚的朋友,和他说告别。
也是和自己说告别。
可,你就连告别也没法吐露无余。
但,你终归向你的朋友交出了你最后的诚实。
你无法说出的告别,
由朋友替你说。
特里,你坐在那儿。
一股香水味飘来,
你像一只幽灵,
迟迟不舍离去。
是的,我们也要告别了,伙计们。
越吵闹的时刻,
越舍不得说再见。
我注视着你离开,
直到你的身影消逝不见。
我依旧注视,
直到整个世界缩小成你。
陬访老人:
钟声敲响,
穿过你的心,我的心,
穿过未来的心。
现在是正午十二点。
一天中太阳最明媚的时刻,
片刻永恒的闪现。
钟声——永恒的项下金铃。
永恒已经有主,
金铃响起时,
主就站在最后一个音符。
你、我就在那儿,
但也只是片刻的闪现。
现在是凌晨十二点,
钟声敲响,
穿过你的心,我的心。
穿过过去的心。
当你循声而至,
永恒已经回家。
陬访老人:
至亲之事,
年纪越大越发难以启齿。
花甲老人找谁谈至亲?
人生百岁,
已是风烛残年。
她的余生比吾太久,
或许还有八十年。
而吾或许只剩八年。
要如何去证明八年可以长过八十年?
无奈,
抬起一棒打走。
留痛在心里延续八十年。